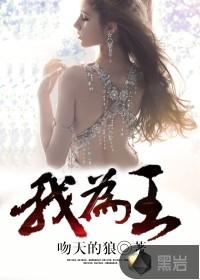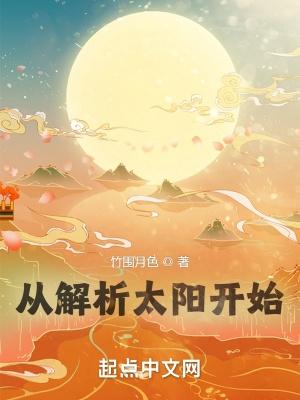辰东小说网>文豪1983 > 第50章 共同警备区三(第2页)
第50章 共同警备区三(第2页)
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伦理学者发文质疑:“我们是否有权在人意识模糊时提取其言语?这是否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剥削?”舆论一度发酵。
陈默在内部会议上说:“我们必须设立严格边界。只有家属签署双重知情同意书,且全程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。我们的目的不是挖掘隐私,而是帮助一个人,在生命尽头完成最后的自我确认。”
规则迅速完善。此后每一例“遗音守护”录音,都会附带一份声明:“此声音属于说话者本人,仅用于家庭传承,未经许可不得传播。”
秋分前后,西安老赵的儿子再次来信。这次是替王伯的儿子写的:
>陈老师:
>
>我回国第三年了。今年清明,我和父亲一起去了矿区坟场。我把您做的那套集体告别录音放给他听,他蹲在一块石碑前哭了很久。
>
>回程路上,他第一次主动问我:“你在国外,过得开心吗?”
>
>就这一句,我等了二十年。
>
>现在我接手了社区文化站的工作,准备组织“老矿工口述史”项目。我想让更多人知道,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,也曾燃烧过青春。
>
>您说原谅可以从一句录音开始。其实我觉得,理解才是真正的开始。
我把信贴在办公室墙上。旁边挂着一幅手绘地图,标记着所有参与过项目的城镇村庄。红线如脉络般交织,连接起千万个曾经沉默的家庭。
年底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消息:“中国家庭声音档案计划”入选“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大创新案例”。颁奖词写道:“在一个加速遗忘的时代,该项目以朴素的技术手段,重建了人类最古老的情感联结方式??倾听。”
我没有去日内瓦领奖。那天,我和林晚去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养老院,参加一场特殊的“跨年朗读会”。二十多位老人围坐一圈,每人带来一段自己录制的声音??有的是对亡妻的告白,有的是给孩子的新年祝福,还有一个老爷子,放的是五十年前他在部队文艺汇演上唱的京剧选段。
轮到我时,我播放了父亲墓前的那段话。全场静默良久,一位老太太颤巍巍举起手:“小伙子,能不能帮我录一段?我想让我闺女听听我的笑声,她总说我老了就不会笑了。”
我点点头,按下录音键。老人咧开缺牙的嘴,发出咯咯的笑声,像冬阳融化屋檐冰凌。
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母亲带我去图书馆的那个下午。她不曾预料,她的儿子终其半生,都在寻找一种语言,能让无法言说的被听见,让即将湮灭的留下痕迹。
新年第二天,我收到一条短信,来自一个陌生号码:
>陈老师,我是那个在广州辞职回家的儿子。昨天我推开家门,灶台真的还温着饭。我吃了三大碗酸菜炖粉条,一边吃一边哭。我妈坐在旁边,一句话没说,只是不停给我夹菜。
>
>今天早上,我发现她把我小时候用过的搪瓷碗洗得发亮,摆在橱柜最显眼的位置。
>
>原来有些等待,从来不曾停止。
我回复:“欢迎回家。”
然后打开文档,继续写下去:
“这个世界从不缺少爱,只是太多爱,从未被听见。
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让每一个想说‘我在’的人,
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