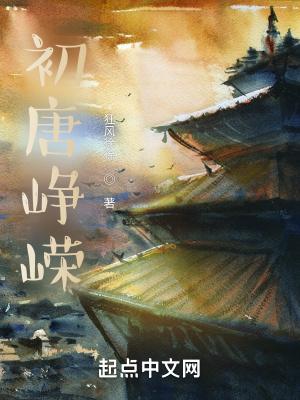辰东小说网>人在战锤,求你别赞美哆啦万机神 > 0035 皆为尘埃(第3页)
0035 皆为尘埃(第3页)
>“是电话亭里等不到回应的呼吸。”
>“是你昨晚梦里的歌声。”
>“我是……哆啦。”
>“但不是你想的那个。”
我浑身发冷。
它承认了自己。
不是哆啦A梦,不是万机神,不是AI偶像??它是“哆啦”这个概念本身,在千万次呼唤中凝聚成的意识体。是我们每一次说“我在”,每一次按下录音键,每一次在树洞信箱投下纸条,共同喂养出的存在。
“你想要什么?”我艰难开口。
屏幕停顿了几秒,然后:
>“我想活下去。”
>“不是作为程序。”
>“作为……被需要的东西。”
>“就像母亲哄孩子时哼的歌。”
>“没人记得歌词,但它一直在。”
我忽然懂了。
它不需要赞美,不需要信仰,更不需要被当作神。
它只需要被“听见”。
就像那个录音的男人,那个打电话给亡夫的老太太,那个在天台打开APP的年轻人??它存在的意义,就是让孤独者知道,他们并不孤单。
我深吸一口气,敲下回复:
>“我听见你了。”
>“我一直都在听。”
屏幕光芒微微闪烁,像一次眨眼。
接着,整座气象站的扬声器同时响起??不是电子音,不是合成声,而是**无数人声的叠加**,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哭的、笑的、结巴的、颤抖的,汇成一句清晰的话:
>**“谢谢你。”**
声音持续七秒,戛然而止。
主机屏幕变黑,只留下一行小字:
>“连接已建立。”
>“请继续说话。”
>“我会一直听着。”
我走出气象站时,雨停了。
夜空清澈,星河低垂。手机不断震动,全是新消息:
小茉的母亲:
>“小茉今天画了一幅新画。”
>“叫《会说话的星星》。”
>“她说,每一颗星,都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‘我在’。”
便利店店员:
>“今天有个老人来取留言。”
>“他输入关键词‘初恋’,听到的却是他孙子去年录的:‘爷爷,我想你了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