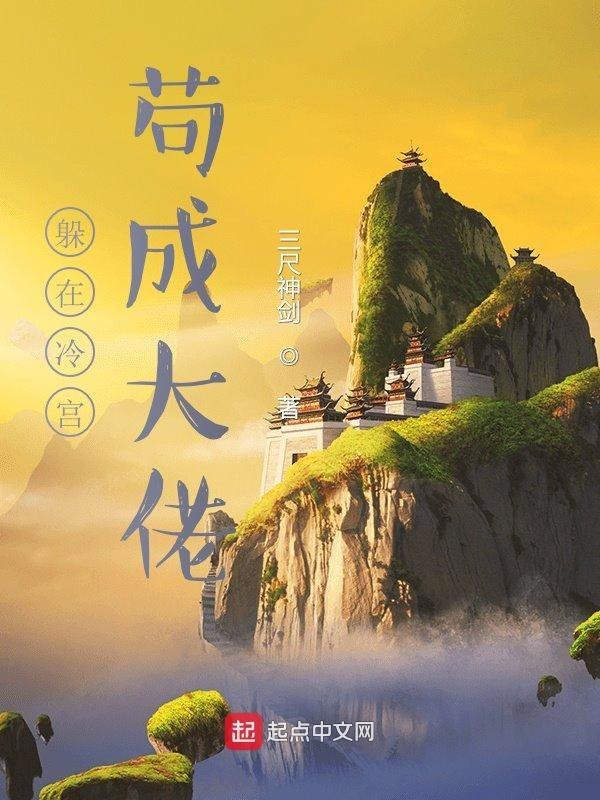辰东小说网>因为有了爱…… > 默默融化的冰雪(第4页)
默默融化的冰雪(第4页)
“哎,哎,别这样说,你那戏就是好,就是好嘛!”“立正”赶忙让客人落座。
“哪里,哪里,很不成熟,很不成熟。那是一出描写战争的戏,我对战争是门外汉,闭门造车,谬误难免。黎政同志戎马半生,还不吝指教。”费博文说着,掏出笔记本来,俨然是一副士耳恭听的模样。
“立正”见对方尊重[3己的态度如此真诚,也就拉着木杆擦炮膛——直来直去地提上了意见。什么步兵应该在炮火延伸的同时发起进攻,而舞台上炮击停止了步兵才上场啦,什么六零炮是曲射炮而演员拿着当初;枪平射啦,什么拚剌刀是些“花花动作”,不合规范啦,等等。费博文非常虚心,未作半点解释,——记了下来。末了,他合上笔记本,感叹地说:“真是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呵!为了使这个戏能臻于完美,我提议,咱们合作来写它好不好?”
话说到这儿,费博文的来意才真正挑明。一出精心构思的戏,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,至此开始了“起”的阶段。为了“起”得自然,前面做了不少铺垫,问题的提出应该说是“既在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”。
“立正”听了,很不好意思,忙说:“哎呀,不行不行,我可没那本事。我初到这种业务单位,对文化工作完,全是门外汉。今后,还要好好向你学习。”
“哪里,哪里,互相学习,互相学习。比如这个戏吧,我缺乏军事知识,希望您一定参加合作。”
“立正”再要推辞,费博文已经将《巧》剧文字本捧在手上,认真地说:“黎组长,您常说文学是党的事业,您来参加这次创作。也是义不容辞的吧!”
黎政听了,神色庄重起来。他双手接过剧本,鞋后跟“嚓”地响了一声,那是个标准的立正动作。
出了“立正”的家门,费博文又去了田局长家。他精心构思的这出戏向“承”的阶段发展了,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必不可少的情节。
“田局长,去省里调演的剧目定下来了吧?”费博文知道田局长的弱点,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问题“那只是初步想法,初步想法。”老实的田局长猝不及防,果然一下子证实了“初少想法”的存在。《绣楼梦》代表地区到省里去,是早已悄悄内定了的。费博文心里很是气愤,又说道:“群众议论纷纷,意见很大呀!”
“唔?唔?”局长听说意见很大,心里有点儿慌乱。
“《绣》剧是廉组长挑头写的,我知道田局长很为难。可是,我们这台戏,是黎组长挂的帅呀!”
“嘿嘿,有那个事吗?”田局长宽厚地笑了,“黎政写戏?他可是个外行呀!”
“唉呀,正因为是外行,才要变成内行嘛。这您还不理解?你捧一个,压一个,得罪了老黎,今后工作恐怕就田局长立刻想到了那天办公室里黎、廉二组长的争执,噢,原来是这样!大概是耳蜗神经失去了平衡感的缘故吧,他感到有点儿眩晕。
“唔,我们再研究研究吧,再研究研究。”
费博文走了。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,这出戏的情节已经发展到了“转”的这一步,事情有了转机。费博文此时是心安理得的。“为艺术而争”,“为正义而争”,他觉得这样做无可非议。
然而,他糈心安排的这一“转”,可把“立正”转苦了。“立正”一连几夜通宵未眠,把《巧》剧本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,果然发现了许多大谬不然之处。他决定,自己要象一个名副其实的作者一样,把所有不妥之处修改一遍,然后再请费博文审定。
那时正值三伏酷暑,“立正”挥着大芭蕉扇在灯下苦战。剧本中那些说话一样的道白还好改一些,可是唱词寘使他作了难。他觉得,那些唱词长而罗嗦,比如“人迹稀鸟飞绝肃杀景象”,倒不如改作“人稀鸟少真偏僻”直捷快当。可是这样一改,那些韵脚就更难以捉摸了。他听说戏词要讲什么平仄,于是就借了一本《中华诗韵》,象小学生查字典一样认真翻了起来。坐得久了,只觉得暑热难耐,头昏目眩。于是,他就打来一桶凉水,将双腿直浸在桶里,头上顶着一条湿毛巾,苦熬苦撑。
看着在灯下挥笔疾书的丈夫,妻子琼枝又自豪又心疼。哼,廉组长有什么了不起!听说五三年在乡公所当个小通讯员,还不是因为编了个小快板在省报上登了登才出了名。老黎那时已经在部队立过三等功了,军报上也登过他的一段《战士诗抄》哩:“大炮轰轰震天响,战士杀敌向前方……”这张小报,如今还珍藏在皮箱里呢。老黎如果一直写诗的话,他如果不是老呆在部队里的话,保不准现在也是一位大诗人哩!
哼,老黎在部队二、三十年,关节炎、胃溃疡、腰肌劳损……部队的“职业病”哪样没沾上?什么苦没吃过?如今,却落得个“外行”、“万金油”受人嘲弄。嘻嘻,这回瞧吧,老黎也是会写戏的,从今后他要变成内行啦!
琼枝尽心地照料着老黎,虽算不¥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,但也确乎是夫妻恩爱、体贴备至了。她不但为丈夫换头上的湿毛巾,换桶里的凉水,并且还买来鲜鱼,细心地剔掉尖剌和骨头,用大米煲成烂烂的鱼粥,为丈夫作夜宵,然而《巧夺桃山寨》修改完毕之际,“立正”还是发烧病倒了。琼枝捧着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,亲自送给了费博文,一切崇拜丈夫的女性都喜爱宣传自己的丈夫,琼枝也不例外。她就象一场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的广播员,把“立正”的“英雄事迹”喋喋不休地四处传扬。
这一来,“立正”马上成了文化局的“新闻人物”。田局长确信费博文反映的“黎、廉之争”情况属实;“小说家”喜滋滋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些生动的“细节”;》“戏篓子”在全局会议休息间隙,用炉火纯青的舞台艺术手段夸张地表演了黎政“头悬梁,锥剌脬”(头顶巾,脚
浸桶)的情景……
四费博文觉得,这出戏的情节发展至此已出现**,“转”机之后,该出现“合”的局面了。但是,作品中的人物各自沿着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,使情节又出现了一串跌宕。
剧团的导演忽然找到田局长,要求把自己撤职。因为,在排《巧》剧的时候,团里居然出现了另一位新导演。
费博文陪着局长到剧团排练场去,果然见到那导演正在给演员们“讲戏”。那备演不是别人,正是抱病亲临排练现场的黎政。他已经示范了剌杀、擒拿等动作,直弄得—身尘土,满脸臭汗。此刻,正在排《突破封锁线》一场的过场戏。
他一边说着,一边伏身在那“铁丝网”上,要一个演员来演练。费博文和田局长未及阻拦,那演员已遵命冲了上去。只听“咚”的一声,痩弱的“立正”即刻倒在舞台上。局长大惊失色,亲自登上舞台搀扶起黎政,好言劝慰他休息,派人把他送回家里去了。
费博文见到此情此景之后的面部表情十分复杂,说不出是乐,是敬,抑或是怜。他悄悄拉着导演,向他透露了自己这出戏的“创作意图”。导演心领神会,答应一切照办。于是,费博文精心构思的“作品”终于到了尾声,出现了“合”的结局。
五田局长眼见“立正”对《巧》剧如此尽心尽力,大有拚上命干的劲头,于是从维护“安定团结”出发,他马上派人打电话给省里,谈及地区欲派京剧、豫剧两个团同时赴省演出。省里那个“一个地区一个戏”的通知,只不过是“原则上如此”而已,执行起来却是可以变通的,当即答复批准了。
于是,《绣》、《巧》两个剧组一边分头赶印剧本,一边做赴省前的试验演出。可是,《绣》剧的文字本送到印刷厂排字,却迟迟未能付印,因为作者名字的排列次序一直定不下来。廉组长提议用“廉习袁”倣笔名,那是用三个作者的姓拼组成的。可是“小说家”和“戏篓子”坚决反对,因为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廉组长一个人的笔名。争论的结局,大家都赌气要推倒重写,每个人都分别写自己的《绣楼梦》,然后从中择优。这样一来,赴省调演他们就被排在了第二轮,《巧》剧自然当仁不让,首先赴省了。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三个人终于清醒了。他们互相抱怨了一番之后,就开始骂起费博文来。进而再一推敲呢,一个小小的费博文决不至于有这么大的能量,关键在于有“立正”做后台。于是,他们就将一腔怨气发泄在“立正”身上。他们扬言,要写一出讽刺剧来嘲弄“立正”这个想当“内行”的“外行”人物。
而“立正”呢,自从当了一回导演之后,就大病了一场,一直卧床不起。但是,《巧》剧赴省之前的演出他仍然坚持去看完了。戏散场之后,他由爱人搀扶着到了费博文家里,激动地对老费说:“戏演得不错,观众‘说,到省里一定能打响的。”
费博文悠然地笑了:“当然,这里面也有您一份功劳。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将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剧本递给了对方。彩印的剧本封面上,“费博文”三个字后面,赫然地署着“黎政”两个字。
黎政看了一眼,摇头说:“谢谢你的好意,可是,这里面并没有我的东西。看完演出,我在剧院里就对田局长说了,我不能挂这个名。”停了一下,他又诚恳而惋惜地对费博文说,“你们这些文人呐,就是太固执、骄傲。如果你能采纳我的修改方案,这个戏本来会锦上添花的。”虽然由妻子搀扶着,但黎政脚下仍“嚓”地响了一声。一个立正,他转身回去了。
费博文疲乏地仰靠在躺椅上,苦笑了。他知道,自己构思的生活中的这出戏也到此唱完了。在这戏里,黎政是个“本色演员”,他毫不做作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。而费博文自己,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内疚带来的酸涩。
不知道在廉组长要写的那出讽刺剧里,黎政会被归入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中的哪个行当。也许,他们会给他涂个小丑那样的“二花脸”。但费博文知道,即使那样,黎政也会保持着“立正”的姿势,因为他有一个“立正”站着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