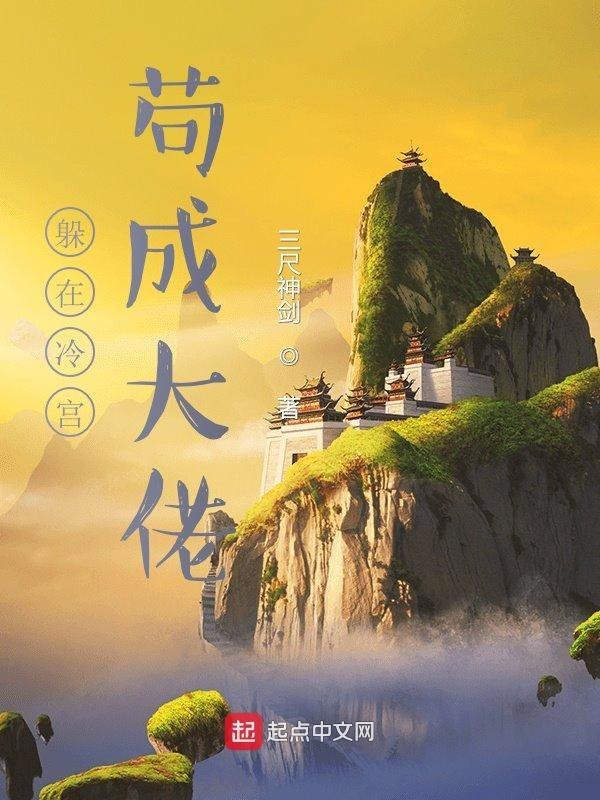辰东小说网>天路难回 > 第十章(第6页)
第十章(第6页)
周栓宝家的院子。天色已晚。
周栓宝坐着小板凳,一边择菜一边抽烟。
王淑兰端着盆尿布从海山家出来,一边往绳子上搭一边说:“这海山还不回来,大礼拜天的,哪儿那么忙?”
周栓宝说:“快国庆了,哪儿能不忙。告诉你,下礼拜起,我也得停休了。”
门一响,乔占魁探进头来:“哟,两口子说知心话哪?我呆会儿再来?”
周栓宝皱眉:“你废什么话!不过你得小点儿声,人孩子刚睡着。”
乔占魁进院:“得,小点儿声。我得跟周大公安人员汇报点儿事儿,求个方便啊。”
周栓宝沉下脸,他知道这家伙没好事。正所谓夜猫子进宅,无事不来。
乔占魁自顾自拉过个小板凳,坐下了。
他是来给儿子求情的,他的二小子乔云标让公安局收容了。
也许是因为那次被周栓宝抓住又放了;心里多少受点触动.乔云标这小子后来变得老实了许多,一直没上街作案。这倒让他那老贼父亲乔占魁看不上眼了。
“小子,”老爷子揉着铁球,这样喝斥儿子,“你不能总让爸爸养活着,对吧?这程子咱们家钱粮可是吃紧。”
“爸,”乔云标说,“我怕让人抓了。”
“嘿!怎么这么熊啊小子?”
“不是,”乔云标转转眼珠,想出搪塞父亲的理由,“我哥不是上朝鲜了吗?我要是现了,不丢他的脸?”
乔占魁语塞。他想起大儿子走后,街坊四邻仿佛忘了他是小偷,对他的那股亲热劲;想起街道上干部们对他嘘寒问暖的关心,心里不禁也泛起一种不知是什么滋味的感觉。
他这个职业小偷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尊重,倒觉得很新鲜。
父子俩就这么熬了一段儿,·后来乔占魁终于忍不住,想出个让儿子化妆成叫花子的主意。
“共产党都同情穷人,,见了叫花子都不嫌弃。这样好。”他说。
乔云标翠不过爸爸,犹犹豫豫地披着麻袋片儿上了街。当他从个老太太兜里掏出个钱包时,他的害怕他的扰豫和他的自责都消失了,他立刻又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偷了。
人学好难,可学坏极容易。
正赶上北京市政府刚刚讨论通过了(北京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》,其中规定人民警察对街头乞丐应随时可以收容。
一个认出他的小贩跑来耳垂胡同,给乔占魁报了信儿。
乔云标那个懒妈顿时背过气去,被大老婆掐人中弄醒之后便嚎陶大哭。大老婆瞪妹妹一眼回自己屋了。乔占魁在院里转了半天磨,一跺脚,来求他一贯看不起的警察周栓宝。
在周栓宝面前,他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但终究有点不好意思地讲了来意。周栓宝听罢站起来:“这事我管不了,就是能管我也不管,我不能犯错误。”
“看看,看看,”乔占魁也站起来,“破尿盆儿,你还端起来了。街里街坊的,你真忍心看我们云标去劳改?”
“不是劳改,是收容。上面公布了乞丐处理办法。你呢,偏让云标装成乞丐上街掏包去。收容了算好的,要是掏钱包抓住了更轻饶不了。”
“可我们云标才14岁。”
“你们云标干那事儿可不像14岁。”
“喝,我琢磨我这嘴就够损的了,没想到你姓周的比我嘴还损。我可告诉你,我们老大云林可在朝鲜打仗呢,我是最可爱的人他爸!这帐怎么算?”
周栓宝叹口气:“就冲这个,我不计较你,你请回吧。”
乔占魁恨恨地看着周栓宝,半晌才吐出一个字:“好。”
我们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,乔云标这次进公安局再出来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。当乞丐被收容自然不会蹲大狱,问题是警察在乔云标身上搜出了钱包和现款。
该着乔云标倒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