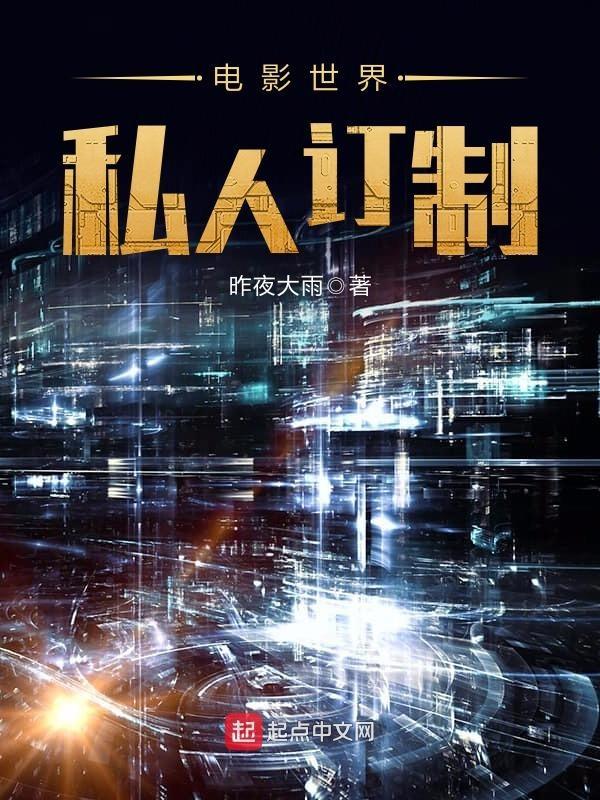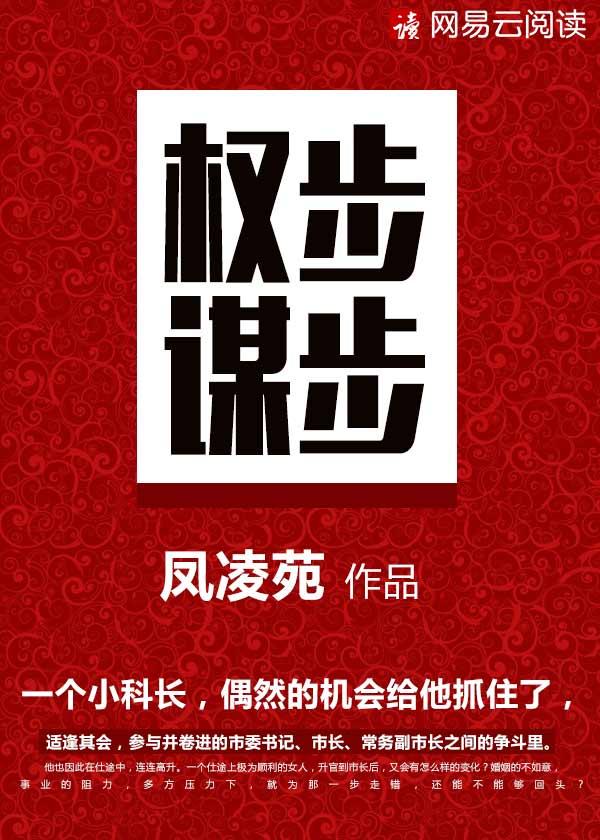辰东小说网>相国在上 > 254人人如龙(第2页)
254人人如龙(第2页)
他走上高台,面对万千信众,声音沉稳如钟:
“我执掌权力,非为私欲,只为不让忠魂白死,不让百姓蒙冤。
我为那些无声者而战??边关将士、田间农夫、市井小民,他们是江山真正的基石。
若天下皆错,我亦不敢称独对,但我必挺身而出,哪怕孤身一人,也要点燃一盏灯,照亮后来者的路。”
话音落下,观微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他转身走入石室,从岩壁暗格中取出一卷泛黄绢册,封面篆书四字:《遗训录?终章》。
李昭接过,指尖微颤。翻开第一页,赫然写着:
>“影司非皇家之私器,乃天下士人共守之道统。每代遴选七人,不分贵贱,不论官职,唯以德行、才识、胆魄三者为凭。七人同心,可废昏君,可立新制,可改律法。然一旦滥用,则自毁其印,永绝传承。”
后面附有历代名单,共九十七人。其中赫然有沈砚之名,位列第三十七代“影议”成员。而最后一栏空白,标注:“待补第七人”。
观微道:“九十七年来,唯有沈砚一人完成了全部使命??他既未贪权,也未避责,更未屈服于任何一方。他用自己的死,唤醒了你。而现在,你要做出选择:是让‘影司’继续作为秘密组织存在,还是公之于世,交由天下共议?”
李昭闭目良久,终道:“公开。”
“你可知后果?朝廷必震怒,宗室必反扑,天下或将大乱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昭睁开眼,“但若连真相都不敢见光,又何谈正义?若连一群读书人都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,这江山还有何希望?”
三日后,一份名为《影司九十七年秘录》的文书悄然流传天下。它详述了百年来“松阁”如何渗透朝堂、构陷忠良、操控储位,也揭示了“镇国影司”的真实来历与职责。每一字皆有据可查,每一条皆附证人名录。
京城震动,江南士林沸腾。数十名年轻举子联名上书,要求设立“监察院”,由科举出身的官员轮流执掌,监督六部与皇权。西北边将亦纷纷响应,誓言“只效忠山河,不效忠私党”。
皇帝连下三道诏书斥责“妖言惑众”,可民心已变。连太子都私下召见陆明远,询问“影议”制度能否纳入新政。
半年后,李昭重返京城,在太学讲坛上宣读《大同新解》,提出“君为民仆,官为公器,法为衡尺”的理念。台下学子泪流满面,齐声高呼:“相国在上!”
他没有纠正。因为他知道,此刻的“相国”,已不再是沈珩一人,而是所有坚守初心者的象征。
一年后,朝廷被迫妥协,设立“御史合议制”,允许民间推举贤士参与重大决策审议。虽然权力有限,却是百年来首次打破皇权垄断。
而李昭再次归隐。这一次,他带着哑女,在朔州创办了一所书院,取名“明心堂”。院中立碑,刻着八个大字:“影出于光,心照山河。”
每逢清明,学生们都会前往望月墩,点燃七盏松脂灯,奏响《礼运大同篇》。琴声悠扬,穿越时空,仿佛回应着地宫深处那具青铜棺的静默守望。
某年冬夜,暴风雪骤起。李昭独坐堂前,听风拍门窗,忽闻远处传来脚步声。一人踏雪而来,全身覆白,摘下斗篷,竟是多年未见的崔元朗。
“我还以为你死了。”李昭笑道。
崔元朗摇头:“我在海外找到了那座黑石屿。岛上确实有庙,庙中有碑,碑文写着:‘吾辈非逆臣,乃守夜人。灯不灭,影不散。’旁边埋着一枚玉玺,上面刻着‘天下为公’。”
他将玉玺放在桌上:“这是‘影社’最初的信物。我想,该还给你了。”
李昭没有接。他望着窗外风雪,轻声道:“不,它不属于任何人。等将来有一天,当百姓不再需要秘密组织来匡扶正义时,它才能真正安息。”
崔元朗怔住,良久,点头离去。
次日清晨,雪停了。阳光洒在书院匾额上,“明心堂”三字熠熠生辉。一群少年背着书箱走来,其中一个指着远方问道:“先生,为什么大家都说‘相国在上’?相国不是已经去世了吗?”
李昭站在台阶上,望着湛蓝天空,缓缓道:
“因为有些人,虽死犹生。他们的名字不在史册首页,却活在每一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里。当你看见不公而愤怒,当你面对强权仍敢说话,那时??你就成了新的‘相国’。”
少年似懂非懂,却又用力点头。
风起,檐角铜铃轻响,仿佛回应着某种亘古不变的誓言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紫宸殿地宫深处,那具刻着“吾弟,安否?”的青铜棺静静躺着,棺前两枚金印并列,一曰“代行监察”,一曰“代行废立”。尘埃落定,余温尚存。
夜半,若有耳力极佳之人俯身倾听,或许还能听见极细微的敲击声??像是有人用指节,在棺木内侧轻轻叩击,三长两短,如旧时密语。
那是沈珩留下的最后讯息,也是历史深处永不熄灭的回音:
**“相国在上……我在。”**